2022-09-07 07:50:56
來(lái)源:北京日?qǐng)?bào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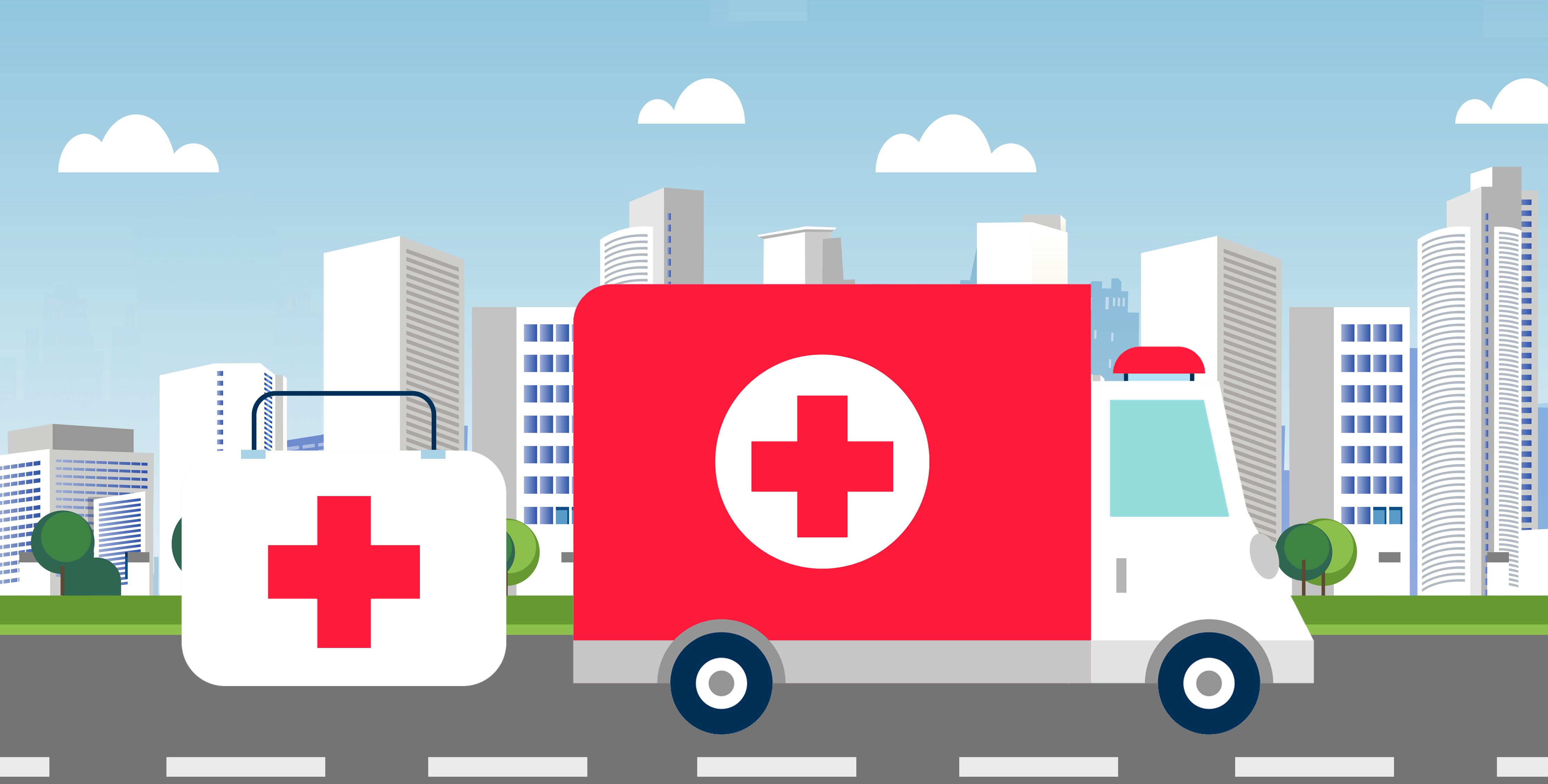 (資料圖片)
(資料圖片)
在他一甲子的藝術(shù)生涯中,曾與朱屺瞻、潘天壽等組織白社研究畫藝,恩師吳昌碩更是贊其詩(shī)書(shū)畫印頗得神韻;1922年任教上海美專,后又于新華美專、杭州國(guó)立藝專(中國(guó)美術(shù)學(xué)院前身)教授花鳥(niǎo)、書(shū)法、篆刻、畫論等課程,與潘天壽、吳茀之并稱“浙美國(guó)畫三老”;他還有一重身份——中醫(yī),早年曾入讀上海中醫(yī)專門學(xué)校的他行醫(yī)問(wèn)診逾二十年,從醫(yī)與從藝貫穿其一生。他就是諸樂(lè)三。
為紀(jì)念諸樂(lè)三誕辰120周年,日前,“藝者仁心——紀(jì)念諸樂(lè)三誕辰120周年藝術(shù)展”亮相北京畫院美術(shù)館,展覽共匯集作品90余件,分“詩(shī)畫”“書(shū)法”“篆刻”“教學(xué)”四個(gè)單元介紹這位國(guó)畫大家的藝術(shù)人生。
諸樂(lè)三師從“海派”巨擘吳昌碩,朝夕學(xué)藝7年,詩(shī)書(shū)畫印皆精,曾被吳昌碩夸獎(jiǎng)“樂(lè)三得我神韻”。“樂(lè)三”之名亦來(lái)自恩師的建議:作人之樂(lè)、詩(shī)書(shū)畫事之樂(lè)、篆刻之樂(lè)。
1922年9月,吳昌碩贈(zèng)給諸樂(lè)三一首詩(shī):“何藥能醫(yī)國(guó),躊躇見(jiàn)性真。后天扶氣脈,本草識(shí)君臣。鶴洛有源水,滬江無(wú)盡春。霜紅尋到否,期爾一流人。”吳昌碩拿中醫(yī)作比自己的得意門生,并非空穴來(lái)風(fēng),而是特有所指。因?yàn)槌怂囆g(shù),諸樂(lè)三還有一個(gè)特殊身份——中醫(yī)。他早年曾入讀上海中醫(yī)專門學(xué)校,行醫(yī)問(wèn)診于中醫(yī)院,從業(yè)時(shí)間長(zhǎng)達(dá)23年。醫(yī)者與藝者向來(lái)有很多共通之處,在諸樂(lè)三身上體現(xiàn)得頗為充分,可以歸結(jié)為一個(gè)“仁”字。諸樂(lè)三長(zhǎng)期浸潤(rùn)吳派藝術(shù),傳承創(chuàng)新,別賦一種濃郁的仁者風(fēng)韻。1924年初夏,吳昌碩作《佛手水仙圖》相贈(zèng),題曰:“仙假手,佛圓光。肱三折,肘一方。赤者劍,青者囊,飲且食兮壽而康。”又題:“樂(lè)三仁兄精通醫(yī)理,寫此贈(zèng)之。甲子初夏,吳昌碩時(shí)年八十又一。”
吳昌碩能夠成為“海派”后期領(lǐng)袖是時(shí)代的必然選擇。晚清時(shí)節(jié),中華民族積弱不振,亟須一種奮發(fā)向上的精神。吳昌碩的繪畫自石鼓文而出,融青銅器上銘文之蒼古渾厚,雄強(qiáng)鏗鏘,點(diǎn)畫間飽含金石味重,蘊(yùn)含著強(qiáng)大的正能量。諸樂(lè)三學(xué)習(xí)吳昌碩,下過(guò)全面的功夫,尤以篆刻為最。他的篆刻從秦漢古璽化出,參以古籀甲骨,自成雄渾樸茂之面貌。他的花鳥(niǎo)畫深得吳昌碩之神韻,于青藤、白陽(yáng)、石濤、八大、任伯年等亦皆有所擷取,用筆蒼勁郁勃,設(shè)色古艷清新,熔詩(shī)書(shū)畫印為一爐,繼承和拓展了吳派藝術(shù)。在詩(shī)書(shū)畫印四個(gè)領(lǐng)域中,諸樂(lè)三尤以篆刻突出,他說(shuō):“篆刻沒(méi)有各體書(shū)法的雄厚功底,光靠‘刻’是達(dá)不到的。沒(méi)有書(shū)法的修養(yǎng),在金石篆刻中就不會(huì)有墨氣。反過(guò)來(lái),在書(shū)畫上,如果沒(méi)有金石篆刻的實(shí)踐經(jīng)驗(yàn),就不會(huì)產(chǎn)生古拙的金石氣息。四者之間,是觸類旁通的。”
作為曾經(jīng)“懸壺濟(jì)世”的行醫(yī)之人,諸樂(lè)三深悟醫(yī)理與畫理相通之道。他認(rèn)為,寫字與畫畫都要虛中有實(shí)、實(shí)中有虛、虛虛實(shí)實(shí)、變化萬(wàn)千,才能表達(dá)出陰陽(yáng)之美。一方印章即是一個(gè)紅與白的陰陽(yáng)結(jié)合體。朱文為陽(yáng),白文為陰,各自與所留空白形成陰陽(yáng)互動(dòng)。字體線條過(guò)粗,導(dǎo)致朱色偏重,在傳統(tǒng)醫(yī)學(xué)中稱為實(shí)癥。若因字體太細(xì),白色過(guò)多,則為虛癥。處理實(shí)癥要瀉之,要刻細(xì)字體或利用邊欄來(lái)減輕朱色。而處理虛癥則補(bǔ)之,即滋陰,加粗字體線條而增加朱色的面積。這樣,才能達(dá)到左右陰陽(yáng)平衡。中醫(yī)強(qiáng)調(diào)天人合一,人與環(huán)境是相關(guān)的。好的藝術(shù)作品必須能反映人對(duì)環(huán)境的感受,同時(shí)順應(yīng)時(shí)代的潮流。
諸樂(lè)三癡迷于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藝術(shù),做學(xué)問(wèn)追求在不同領(lǐng)域中的“會(huì)通”。他的書(shū)法追隨吳昌碩的足跡,于蒼古渾厚中見(jiàn)雄渾飛動(dòng)。他對(duì)楷、行、草、隸等書(shū)體進(jìn)行了全面研究,尤以篆書(shū)和甲骨文為甚。他筆下的花樹(shù)竹藤,常化作篆、狂草合一的筆法,寫出蜿蜒盤郁的姿態(tài)。創(chuàng)作于1947年的《瓦雀芭蕉》在恩師吳昌碩的基礎(chǔ)上又生發(fā)出新意。兩只麻雀立在蕉葉之上,一只飛于其間。芭蕉以篆書(shū)寫其線,點(diǎn)其色,蒼郁飽滿,綠意盎然。1959年的《桃花》將吳昌碩典型的縱式對(duì)角線構(gòu)圖橫放過(guò)來(lái),以右側(cè)頑石為重心,在中部蔓生出一棵桃樹(shù),向上方生長(zhǎng),紛披向左右。另一枝干向左發(fā)展,飽滿的花朵綴滿枝頭,并有一枝回旋向右,與頑石呼應(yīng)。滿紙粉紅,春意婆娑。而在1974年創(chuàng)作的《棉花》中,諸樂(lè)三仍采用吳昌碩最喜愛(ài)的對(duì)角線結(jié)構(gòu),題材卻換成了老師從未畫過(guò)的棉花,因此要在色彩的選擇上另辟蹊徑。諸樂(lè)三以紫色染根莖,以摻了紫色的墨汁繪葉片,盛開(kāi)的棉桃上以藍(lán)色復(fù)染輪廓線,反襯花朵的潔白。他在題詩(shī)中說(shuō):“花開(kāi)吉貝白茸茸,閃閃銀光耀碧空。老筆紛披無(wú)俗慮,牡丹不畫畫棉叢”,確實(shí)達(dá)到了“閃閃銀光”的效果。而牡丹是吳昌碩最為鐘愛(ài)的題材之一,諸樂(lè)三自然對(duì)恩師的畫法極為熟悉,但他在題材上有意拉開(kāi)距離,為的是破一下既定的范式,這樣才能開(kāi)拓出新的格局。
這一創(chuàng)新精神也始終貫穿在諸樂(lè)三漫長(zhǎng)的美術(shù)教育生涯之中。自1922年,他應(yīng)劉海粟之邀,于上海美術(shù)專門學(xué)校講授中國(guó)畫算起,其從教時(shí)長(zhǎng)超過(guò)一甲子,講授過(guò)花鳥(niǎo)、書(shū)法、篆刻、古文、畫論、詩(shī)詞題跋等多門課程。他還參與起草了新中國(guó)高等美術(shù)教育史上第一個(gè)本科書(shū)法篆刻專業(yè)的教學(xué)大綱,讓這門傳統(tǒng)藝術(shù)得以在現(xiàn)代教學(xué)課堂中延續(xù)其精華。
早年間,吳昌碩贈(zèng)給諸樂(lè)三的詩(shī)中提到:“霜紅尋到否,期爾一流人。”“霜紅”指傅山,這位博學(xué)大儒精通經(jīng)史,兼通先秦諸子,又長(zhǎng)于書(shū)畫、醫(yī)學(xué),著有《霜紅龕集》。吳昌碩希望自己這位曾經(jīng)學(xué)習(xí)并從事過(guò)中醫(yī)的弟子,能夠成為像晚明著名醫(yī)師傅山那樣的人,一個(gè)于社會(huì)于藝術(shù)都有所貢獻(xiàn)的人。對(duì)于老師的殷切期盼,諸樂(lè)三以《缶師示五律一首和韻奉和》回應(yīng),他寫道:“詩(shī)格高無(wú)上,輪囷氣自真。裛(浥)奇驚俗眼,多難見(jiàn)完人。蜃幻空樓閣,途窮盡棘榛。莫談離亂事,同醉玉壺春。”諸樂(lè)三以“醫(yī)者仁心”耕耘在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美術(shù)教育的園地之中,在桃李滿天下的同時(shí),亦在畢生所傾心的書(shū)畫篆刻中得到了美好的人格升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