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2-09-02 07:52:22
來源:北京青年報
“如果這個世界對你不好,你可以忍,忍不了可以反抗,只要不丟掉驕傲。任何東西都可以丟掉,除了驕傲。”“你不能流淚,你流淚了,他們就贏了。”
幾乎所有人在青春時,都說過類似的“傻話”吧。哪怕是說給別人,其實也是說給自己。只是大多數人忘了,曾經的孤單與疼痛——多少年后,我們用一句“那時還不懂事”搪塞自己。
好在,《膽小鬼》還沒忘,并把這些寫進臺詞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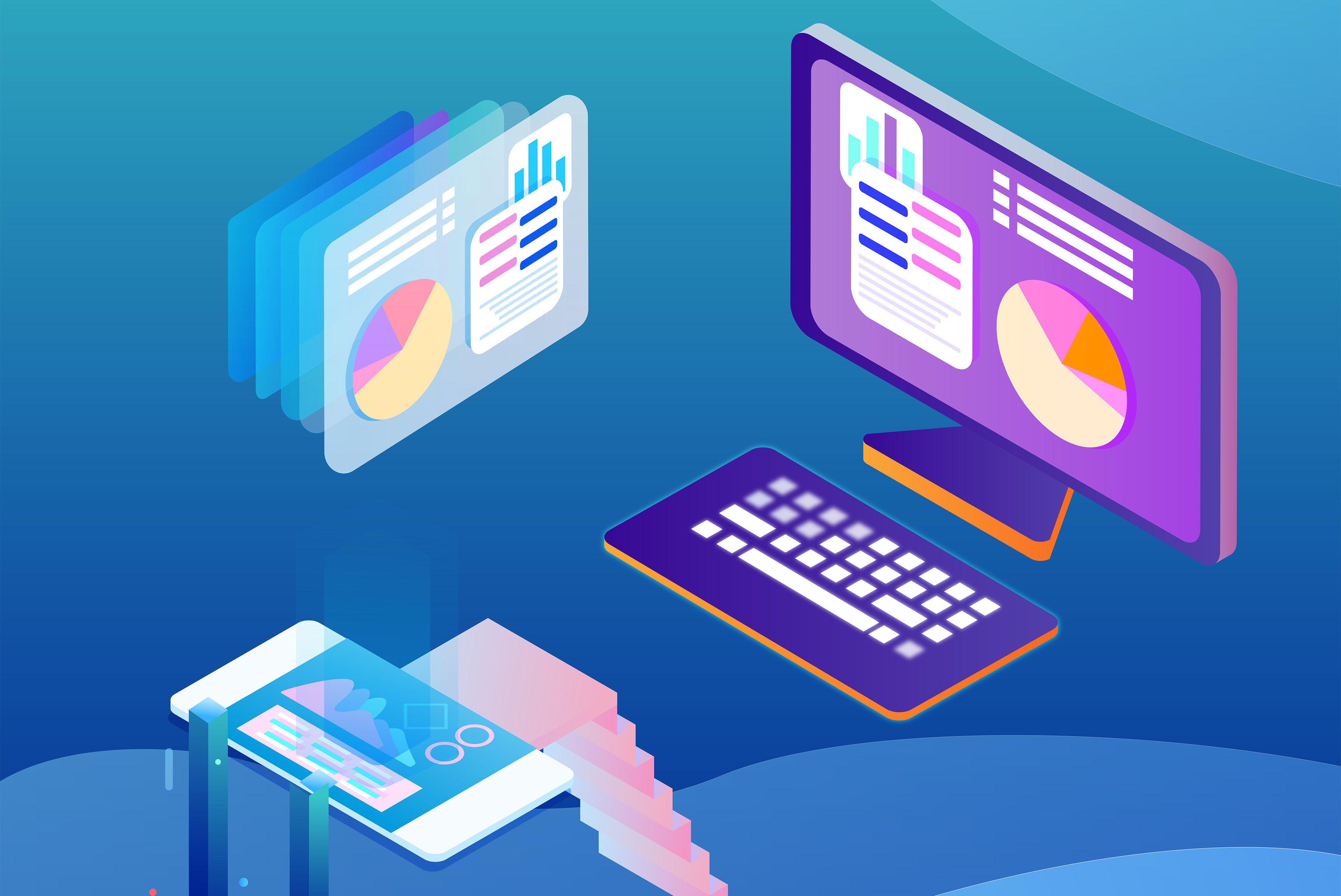 (相關資料圖)
(相關資料圖)
這部鄭執原創、張曉波導演的連續劇似乎平淡無奇,卻直指人心。它用撕開傷口的方式,喚醒了觀看者沉睡在記憶中,似乎早已“死去”的自己。
每次青春都充滿殘酷,每次青春都鮮血淋漓。但單純、憧憬、受傷、無力、絕望,總好過麻木、遺忘與虛偽。
《膽小鬼》并不完美,但它絕對真誠,這個“沒有最虐,只有更虐”的故事屬于所有年輕過的人。當我們越來越不知道自己是誰、什么是愛、為什么要活著時,《膽小鬼》平靜地說:其實你也曾這樣真誠過,那是永遠不能忘掉的。
生命之花還沒盛開,便已凋謝
《膽小鬼》的講述,從東北某城一所重點高中的四個學生開始。
男主角秦理(歐豪飾)是數學天才,深得老師喜愛,卻背負原罪——他的父親是搶劫殺人犯,被判死刑,爺爺一氣之下癱瘓在床。從沒感受過家庭溫暖的秦理自幼體弱,飽受同學欺負,幸虧鄰居兼同學王頔(侯雯元飾)孔武有力,從小到大幫他出頭。
高二時,一直在藝校學舞蹈的黃姝(王玉雯飾)突然插到秦理、王頔所在的班,她像一道陽光,照亮了秦理的人生。
黃姝靚麗有才藝,但心存隱痛。她的母親有精神病,且參與傳銷,被警方盯上。母親原本可能也是藝校生,她不想讓女兒重復自己的痛苦人生,堅決把女兒轉到重點高中,可黃姝跟不上功課,加上她曾在酒吧打工,靠跳舞賺錢,同學們背后指指點點。
兩個弱者——黃姝與秦理,因彼此同情,越走越近。
秦理沒想到,他與王頔的關系因此發生了微妙變化,好友終成陌路。更麻煩的是,愛讓他忽略了,他只有一種方式改變命運——考上大學,可他高三時卻被學校開除了(目前尚未播出原因,應與黃姝有關)。
不論秦理如何幫助黃姝,黃姝怎樣努力,她終因成績不佳,被重點高中除名,只好又回到藝校,而送她離開藝校的母親卻失蹤了。母親此前曾說,要辦一件大事,這樣就有錢了,可以讓女兒脫離苦海。從劇情看,母親可能已被黑社會殺死。
在重點學校就讀的經歷,燃起黃姝的上進心,她想考大學。于是,黃姝回酒吧跳舞,以積攢學費,雖然明知會遭小流氓們的糾纏。黃姝寄宿在舅舅家,舅舅私開家庭牌桌,每日喧鬧不已,為讓她專心學習,秦理專門給她找了一間安靜的小平房……
然而,當警方再次找到黃姝時,她已是一具尸體。
愛情悲劇背后,是時代之痛
上世紀90年代,整個社會突然被消費主義裹挾。
從宏觀看,經濟增長壓倒一切,商品經濟繁榮、信息爆炸、社會流動性增加;從微觀看,則是興奮與沮喪、狂歡與惶惑、追逐與失落并存。遺憾的是,少有文藝作品記錄下這一過程,以致我們常常無法理解當下。
《膽小鬼》多少保留了時代的痕跡。
在《膽小鬼》的世界中,有語文老師的拳拳苦心,也有新來數學老師的誤會;有同學們起哄架秧子,也有課間沖突的血腥;有殺人犯父親難以言說的、對兒子的愛,也有老警察馮國金對家庭的愧疚……消費大潮沖擊下,一切穩定的都變得動搖,一切堅信的都變得可疑,一切有答案的都變得曖昧難明。
當警察得知秦理的父親一次就搶走120萬元,彼此驚嘆:“咱們這輩子,加起來能掙這么多錢嗎?”答案是根本不可能。老警察馮國金(王硯輝飾)在審訊時,好奇地問:這輩子,多少錢才算夠?
秦理的父親說:多少都不夠。
金錢重新劃分了社會:在好人與壞人之外,富人與窮人成了新鴻溝。可舊規則的陰影揮之不去。
秦理的父親為表達對老警察馮國金的感謝,被槍斃前接受了媒體采訪。作為反面教材,他的遺言在廣播中被一遍遍播出。沒人想過,這將給秦理帶來怎樣的傷害。習慣暴力是生活的必修課,正如黃姝知道身邊每個男人都想占有她,“好學生”秦理也被逼得屢屢揮拳。他們太早覺醒了,不知道命運的大門依然窄小——上不了大學,就將被命運套牢。
太多的同代人是在大學校園中才發現自我,才開始成長,才意識到生活還有辛酸的一面。秦理與黃姝能堅持下來,只靠一個借口:明天。總有一天,他們會逃離現實,走進新天地。然而,夾縫時代既可能是“新與舊的好處”的疊加,也可能是“新與舊的壞處”的疊加。命運太不照顧黃姝了,她最終被吞噬,秦理從此只有仇恨、再也不相信明天。
《膽小鬼》好看,因為它在一次愛情悲劇的螺螄殼中,裝下一代人悲歡離合的道場——他們背向傳統,選擇顛沛流離,假裝忘掉責任與愛,他們如此盲目地上了路,卻忘了,苦難會有長長的回聲,這回聲將扭曲他們的孩子的命運。
有創作真誠,才有結構優勢
在黃姝與秦理的愛情悲劇之外,還有王頔與馮雪嬌的愛情悲劇。
馮雪嬌是老警察馮國金的女兒,家庭穩定,但父母工作繁忙,壓抑了她的成長空間。她放棄自尊、矜持去追求王頔,王頔卻半推半就。他不愿放棄和秦理的友誼,后者讓他更像男人;此外,他渴望一份征服別人的愛情。
王頔與秦理分道揚鑣后,10年未再見面,因為沒考上大學,王頔的生活無比狼狽。他的家庭原本充滿小市民的明理、熱心與溫情,在市場化初期,靠擺路邊攤,尚能過上較體面的生活。然而,隨著競爭激烈、家人患病,他才發現,美好生活本是易碎品。再見馮雪嬌時,王頔依然是弱者。
世上大多數人要為生存而奮斗,主人翁只在傳說中。王頔的不幸,在于教育讓他堅信后者,現實卻逼他接受前者。他不知道放下負罪感該如何生活,于是,他被鎖在記憶中,無力自拔。
《膽小鬼》采取了一個討巧的結構:將兩段校園愛情與破案過程穿插在一起,“用破案帶節奏”“用青春故事帶情緒”。
不可否認,“用青春故事帶情緒”也有尬戲,但始終未偏離“消費主義大潮下”這個基本設定,努力呈現出“時代的功利追求”與“校園中的虛假精神”之間的落差。于是,《膽小鬼》營造出悲劇氛圍:毀滅是注定的,懸念只在毀滅的方式。黃姝掛在嘴角的燦爛笑容,與她尸體上的可怕圖案,形成鮮明對照——那也是一個時代的傷口,是無數經歷者心中說不出的隱痛。任何一次飛馳向前,背后都會有追不上車的喘息聲,忘掉這些聲音,也是一種背叛,它讓飛馳本身難以持續。《膽小鬼》的結構確實不錯。
細節的粗糙,不應忽視
當下影視劇普遍存在一大問題:重結構、輕細節。大量細節是從別的作品中“看”來的,或是編出來的,而非從生活中采集而來。相比之下,《膽小鬼》尚屬精細。
比如王頔與秦理住的老式單元樓,樓頂無護欄,卻是孩子們的活動空間;鑰匙串上的折疊剪刀,確曾風靡一時;舊式國營大工廠的封閉結構和毫無個性的雕像;當時的校園秩序,學生食堂只能站著吃飯,以及東北學校廁所的樣式;包括馮雪嬌在男廁所門口大吼,震撼所有正在方便的男生……都體現出創作者觀察生活的功力。然而,秦理直到高二還不會騎自行車,學會后馬上就能帶人騎行;當年秦理給王頔買的籃球,10年后依然還在……也有“為煽情而編造”的問題。
為突出懷舊感,校園里的鏡頭大多偏紅,可透過濾鏡,依然能看出教室門框、黑板框等過度嶄新,學生課桌上既無涂鴉也無刀刻痕跡,甚至連漆皮都沒掉……為救秦理,王頔用椅子將同學拍倒,椅子上的木頭完美地粉碎、向四面崩裂,顯然也是從武俠片中借來的俗套。
在《膽小鬼》的校園中,沒有青春期的扭捏作態、自我戲劇化,沒有不成熟人格,只有好人與群氓的對立,甚至這些青春期的孩子們都不反感家長,顯然是被過濾后的記憶——創作者只記住成長時的光彩,忘掉了成長時的幽暗。
這呈現出個性創作的二元困境:主體性不強,創作者對青春的獨特理解就不會如此深入人心;可主體性太強,創作者又會把自己的誤會當成事實,不自覺間露出粗糙。
觀察生活,有效積累,而不是為了主題、情緒等制造細節,這讓《膽小鬼》擁有了催人淚下的力量,可《膽小鬼》并沒在根本上解決細節虛假的問題,考慮到青春記憶不是萬能藥,今后遇到不熟的題材,創作者們該怎么辦?隨著記憶材料一次次被消耗,會不會有一天,又回到“坐在辦公室里搞怪的”老路上?所以,不應忽視這些粗糙。